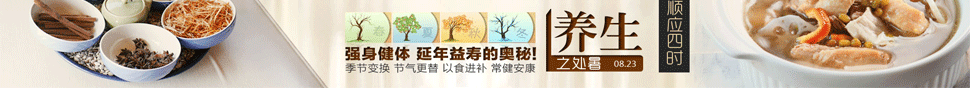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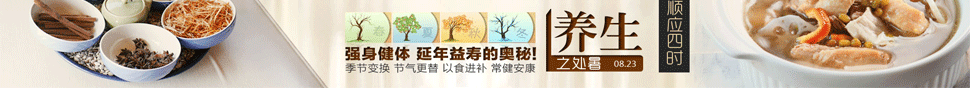
六朝槟榔嚼食习俗的传播:
从“异物”到“吴俗”
郭硕
槟榔在汉代以前是一种南方异域边缘的“异物”,其大规模内传实际上发生在吴晋之际。刘宋以后,关于槟榔嚼食的许多“异俗”逐渐成为南方本地的风习而在士人社会中流行。南北朝后期,嚼食槟榔成为了北朝人眼中南朝“吴俗”的典型特征,并为北方士人所模仿。以槟榔为代表的“异物”在与士人发生直接接触以后,代表其文化意义的“异俗”逐渐在书籍的传抄和文人的咏赏过程中得到积淀,附加在其上的文化价值也由此产生。
槟榔是产于热带地区的一种植物,其果实是著名的药材和嚼食用品。槟榔有悠久的嚼食史,特别是六朝时代,有关槟榔的药用及嚼食的记载屡见诸史料,唐宋以后关于槟榔的记载甚至很少有超出六朝记载之外的内容。作为只能在中原范围之外种植的“异物”,六朝时期槟榔能够在非种植地区引发嚼食的潮流,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槟榔药用价值方面有许多研究,台湾学者对槟榔文化的源流也有一些研究①,但目前各研究主要集中于闽台及岭南地区的种植与食用,也还有诸多疏误。对于槟榔嚼食源流特别是六朝时期内地的槟榔嚼食潮流以及深藏于现象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则未予深究。这种代表异域文化的物产与南渡的中原文化在六朝的融合过程正是本文所试图加以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汉代的槟榔:
存在于异域与边缘的“异物”
一般认为对槟榔的记载最早出现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留落胥邪,仁频并闾”中的“仁频”一词,《文选》李善注引《仙药录》云“仁频即槟榔也”[1]()。《史记》司马贞索引引姚氏云:“槟,一名椶,即仁频也。”[2]《汉书》颜师古注亦称“仁频即宾桹也”[3],“宾桹”当是槟榔的同音异写。值得注意的是,三种注释所引用的依据似乎不尽相同,看来并不是简单的互相传抄的结果。比对《上林赋》中提到的诸种果类,确有许多产于热带的。“胥邪”,《史记》司马贞《索隐》引《异物志》云“实大如瓠,系在颠,若挂物。实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里有肤,厚半寸,如猪膏。里有汁斗余,清如水,味美于蜜”云云,亦见于《齐民要术》卷十“椰”条所引同书[4](),当是椰子;“荅沓离支”中的“离支”,晋灼云“大如鸡子,皮粗,剥去皮,肌如鸡子中黄,味甘多酢少”,应即荔枝,均可算是热带植物。看来,诸家注释所称“仁频”即是槟榔的说法,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不过,“仁频”这一称呼仅见于此,后世文献中多见的“槟榔”等称呼与“仁频”差别较大,其原因值得进一步追寻。实际上,“胥邪”“离支”这些岭南作物的称呼,虽然读音与后世称呼相近,但此种写法在后世也已经不见。而《上林赋》该段提到的其他物种,如“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所见的多数果名,却与后世相同或相似。看来汉代以后“槟榔”这一名号将“仁频”完全替代,其中原因需要做出解释。现存史料中,《三辅黄图·卷三》也可见有汉武帝移植“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5]()的记载,说的可能与《上林赋》是同一事。按《三辅黄图》据何清谷先生援引陈直先生说为东汉末曹魏初人所著,应该说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不过,《黄图》也有许多后世窜入的内容,陈直、何清谷先生均认为今本《三辅黄图》与颜师古注的关系,是“《黄图》用颜注,而非颜注用《黄图》”[5](前言,5),则《黄图》的这段记载是否系敷衍颜师古注释而成,实未可知。
需要着重提出的是,在《黄图》里已经没有“仁频”“离支”这样的名号,而是使用后世常见的称呼了。按《上林赋》极尽铺张夸饰,司马贞引晋灼曰:“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珍奇,不系于一也”,广泛述及当时所能见到的乃至出于想象的各类奇珍异物,可以认为,“仁频”也是作为极罕见的“异方珍奇”而出现在汉代人的心目的。有研究指出,“槟榔”是马来西亚语Pinnang的对音,“仁频”是爪哇语Jambi的对音[6],也就是说,这两个词语乃是来自不同语言的音译词。“仁频”这种岭南“异物”离汉代人的生活太远,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连名称都没能传承下来,以至于最后被后世新译的名称“槟榔”代替了。也就是说,汉武帝时期人们发现了槟榔等“异物”,但对它的认识并没有深入,后世可能还有一个重新发现的过程。
现存史籍中对槟榔进行详细介绍者,学界一般认为的是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这一点需要辨析。《齐民要术》引用的这则不注作者的《异物志》中一百多字的轶文,对槟榔的种植方法、形态、槟榔果的食用方法、药用价值都有清晰的记载。杨孚生卒年已无法详考,吴永章先生在《异物志辑佚校注·前言》中认为其主要活动于在汉章帝至和帝时期,所著《异物志》到北宋以后方才亡佚。不过,最早著录杨孚《异物志》的《隋书·经籍志》之地理部,有“《异物志》一卷,后汉议郎杨孚撰”,又有“《交州异物志》一卷,杨孚撰”[7],交趾刺史部改称交州在汉建安八年(),时间远在汉章帝时期百余年以后,因此吴永章先生认为《交州异物志》“决非杨孚书的原名”[8]。《隋志》对《异物志》和《交州异物志》分别著录,则二者到底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都已不能确定。另外,关于杨孚于章帝时期出任议郎的最早史料乃是出于明代,《后汉书》出现的“杨孚”记载也并无关于《异物志》的蛛丝马迹,根本无法确定这些杨孚与创作《异物志》的杨孚是否是同一人,因此吴先生关于杨孚生平的说法实际上恐怕很难坐实。
现存古籍对《异物志》中槟榔相关记载的引用,分见于《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字基本相同,应系同一史源。不过,三书对《异物志》该条史料的引用,全都没有注明即是杨孚的《异物志》,而据王晶波《汉唐间已佚〈异物志〉考述》一文所列举,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以某某《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共有22种之多,完全以《异物志》命名的有7种[9],多数出于隋以前。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则史料是出自于杨孚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②,亦即东汉时期是否有关于槟榔的记载也是不能确定的。不过,从这则史料的引文出处的处理来考虑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线索可循。《齐民要术》中,《异物志》的史料排在俞益期《与韩康伯笺》《南方草物状》之后,《林邑国记》《南州八郡志》《广州记》之前。韩康伯《晋书》有传,事迹颇合,则俞益期是晋朝人无疑;《南方草物状》一般认为是嵇含作,也是晋朝人;《林邑国记》《南州八郡志》《广州记》三种,一般也认为是晋朝著作③。《艺文类聚》将《与韩康伯笺》按文体分入笺一类,而在《异物志》的史料前面增加了周成《杂字》、李当之《药录》《广志》三种史料,将《林邑国记》的史料调入《异物志》前而作《林邑记》。周成《杂字》,《隋志》有著录,成书于曹魏;李当之是华佗弟子,亦是曹魏时人;《广志》据说是西晋郭义恭所作,成书时间皆应在《与韩康伯笺》之前。《齐民要术》和《艺文类聚》可以发现二书对同类材料的排序,大体都是依据出现时间先后而排列的,极少有将汉代的材料排列在魏晋材料之后的情况。如果《异物志》这条史料没有窜乱的话,有理由相信它是出于晋代而非东汉。当然退一步说,若依吴永章先生考订,写作《异物志》的杨孚本是广州人,如果《异物志》中关于槟榔的记载真是出自杨孚的话,出身于岭南的杨孚将原产岭南槟榔作为“异物”写入自己的著作中,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可能存在的。不过这顶多也只能说明,在东汉时期的人们看来,槟榔只是一种来自异域与边缘的“异物”。
南越地区最早进入中国版图应该是秦始皇时期,不过位于汉帝国边缘的南越地区一直都被认为是“异域”的范畴。直到汉献帝建安年间设立交州,这一地区才真正成为和内地相似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不过这时候的汉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军事上的征服和物种的传播是两个范畴,对于槟榔这种无法适应较为寒冷气候的作物来说尤其如此。整个汉朝,非但槟榔树只存活于帝国的边缘地带,槟榔果乃至于槟榔的概念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顶多就是某种只闻其名而难见其物的“异方珍奇”而已。
二、槟榔“异物”内传的过程:
基于吴晋之际几种史料的辨析
从现存文献来看,对槟榔的记载突然增多的时期是孙吴到西晋初期,亦即公元3世纪中后期前后。经笔者整理,目前可见成书时间在3世纪中后期而有对槟榔记载的有如下数种:三国吴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曹魏的李当之《药录》、周成《杂字》,西晋初吴人张勃的《吴录》、西晋时期嵇含的《南方草木状》、郭义恭的《广志》、左思的《吴都赋》。这些史料多经过前人的归类整理,特别是《齐民要术》以及《艺文类聚》等类书对槟榔的某些方面有详略不等的分类介绍或描写,可能是当时所能见到的相关资料的最早、最全的资料的汇编。因此,可以将这些史料为基础作具体的分析。
为方便讨论,需要对记载槟榔的相关材料作一个简单的分类。第一种为《异物志》类记述“异方珍奇”的书。这类著作从时间上出现得较早,主要有三国吴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如果将范围放得更广一点,《南方草木状》《广志》等书也可算这一范畴。据王晶波说,《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9],应当大体符合事实。今以《文选》卷五《吴都赋》李善注所引,成书时间较早而记载较为完整的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为例略作分析:
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1]()
据《三国志·薛综传》载,薛莹乃是薛综之子,而薛综少时避乱至交州,在孙吴曾长期担任合浦、交趾等地太守,后又从征至九真,是孙吴经营交州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薛莹自己也到过广州。因此,薛莹的记载当是出于亲身经历,应属第一手资料。从李善注所引材料看来,薛莹对槟榔树及槟榔果的形态、食用方法、产地皆有简要介绍,但皆是平实地记载和介绍一种交州的“异物”而已。实际上,其父薛综曾上书给孙权称交州地区“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10](),明确称对交州的经营就是为了当地的异物充备宝玩,而非“仰其赋入”。又,《三国志·卷四九·士燮传》称“作守南越”的士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10](-)可见薛综之说不虚。薛莹将槟榔作为“异物”详细介绍,可见在当时人看来,槟榔确实是一种刚开始为士人夫认识的新异物产。
第二类为史书的《地理志》。目前可见最早记载槟榔的是张勃的《吴录》,成书时间上应该比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略晚。《太平御览》《齐民要术》所引几段关于槟榔的记载均见于《地理志》。《太平御览》引《吴录·地理志》云:
交趾朱?县有槟榔树,直无枝条,高六七丈,叶大,如莲实房,得古贲灰,扶留藤食之,则柔而美。郡内及九真日南并有之。[11]()
又,同书引《吴录》曰:
交趾朱鸢县有槟榔,正直高六七丈,叶大如盾。[11]()
按“?”字即“鸢”字古体,内容相似,因此这两条史料应该是来自同一史源,偶有文字出入当是传抄过程中的窜乱,因此我们可以将两段文字组合起来作分析。细绎史文,“交趾朱鸢县”应是地名的著录,其后的文字才是记载该地的物产。如果拿这两段史料和上引薛莹的《荆扬已南异物志》作对比的话,就能发现其内容几乎与薛书完全吻合,只是将“交趾朱鸢县”提至文首,后文则以“郡内”代之。至少就这一段文字而言,薛书应该就是《吴录·地理志》该段史料的史源,张勃仅仅是将其改成了地理志的书写格式并略作删改而已。《吴录·地理志》对《荆扬已南异物志》内容的沿袭,正是槟榔的相关知识从亲历者的记载向史书阅读者传播的开始。另外,《齐民要术》中还引用了一段《吴录·地理志》的史料提及了槟榔:“始兴有扶留藤,缘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槟榔。”[4]()这一条应是记载始兴郡的物产“扶留藤”,顺便提到了可以与槟榔同食。记载他种物产还提及可以和槟榔同食,则可见槟榔在交州物产中的地位较为重要。《吴录·地理志》著录各地物产时提到槟榔,说明时人对槟榔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异物志》一类著作专门介绍各地奇异物种的范畴而正式进入史书之中,对有关槟榔知识的传播起到不同的作用。
第三类是文学作品。左思的《吴都赋》是目前可见这一时期最早提到槟榔的文学作品,时间约略与张勃《吴录》相当,或者略晚。此外,俞益期的《与韩康伯笺》是稍晚一些的作品,我们也可合并考察。左思《吴都赋》虽赋的是“吴都”建邺,但其中却提到多种岭南的佳果,“其果则丹橘余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荫。龙眼橄榄,探榴御霜。”[1]()顺便提及,左思将槟榔与柑橘、荔枝、椰子、龙眼、橄榄等水果并列,与前引《三辅黄图》中所提及的汉武帝移植“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诸种水果品种,是基本一致的。晋初北人对南方物产的认识水平,应当是不及南方的薛莹、张勃的。以“赋”这种文体铺陈异物的特点,也可以认为,在北人左思那里,槟榔等热带作物,也仍旧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奇珍。不过,曾经导致“洛阳纸贵”的《吴都赋》,影响非常广泛,赋中提及了槟榔这一佳果,对槟榔这一南国佳果走向士人世界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俞益期《与韩康伯笺》今存有近二百字,应该说传播也是比较广的。文学作品的对槟榔传播的作用,本不在于增加有关槟榔的知识,而在于推动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一种佳果,并由此引领士人食用的风潮。
另外还有两种文献提及槟榔,便是成书于曹魏的周成《杂字》和曹魏李当之的《药录》,需要作简单地辨析。这两则材料最早为《艺文类聚》所采用,周成《杂字》称“槟榔,果也,似螺,可食”;李当之《药录》称“槟榔一名槟门”[12]()。二者共同的特点就是字数非常少,对槟榔的介绍非常简单。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是《艺文类聚》关于槟榔排列最前也当时编著者认为最早的材料,按理说应该将基本内容都予以收录,不会简简单单就收录数个字。最可能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对槟榔的认识非常浅,二书的记载原本就很简单,所以在《艺文类聚》之前成书的《齐民要术》甚至都因为其记载因为太简单没有价值而不予收录。按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八》称“大要岭南使用”而“自常和合,贮此之备,最先于衣食耳”的“葛氏常备药”中便有“槟榔五十枚”。[13]葛洪流落岭南多年,其认识槟榔的药用价值和并经常使用当属正常,但从文意看,其“常备”槟榔却是因为价值重要但难以获取。比葛洪早上百年又处于与南方隔绝的曹魏的李当之,要获取和使用槟榔,其难度比长期在岭南生活的葛洪当然要大得多。因此,曹魏时期周成和李当之对槟榔的认识,并没有超出汉代人对“异物”认识的程度。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还原出孙吴以后南方士人对槟榔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在汉末人们逐渐了解到知道南方的异域与边缘有槟榔这么一种“异物”,随着孙吴对交州的开发和控制以及海外交往的频繁,最早一批进入交州地区的士人开始将槟榔记入《异物志》一类记述“异方珍奇”的书。也随着吴人对交州地区的实际控制加强,张勃等人将《异物志》一类的记述转写入史书,促进了有关槟榔的知识的传播。入晋以后,槟榔作为一种佳果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达,这些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推动槟榔这种“异物”逐渐进入士人的生活。
三、“异俗”到“吴俗”:
南朝槟榔嚼食习俗的流行与传播
从孙吴到东晋,从《吴都赋》等材料中虽可以看出槟榔是一种可供食用的佳果,但对于士人嚼食槟榔却没有详细的记载。汉族社会在最初引入槟榔的时候可能主要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houpua.com/hpzz/55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