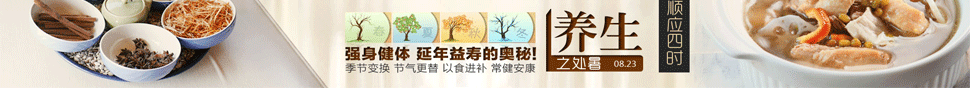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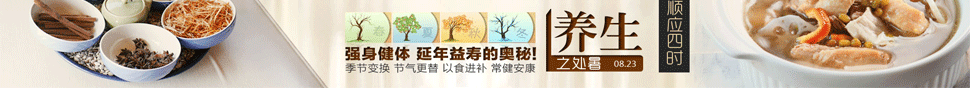
醉美秦直道
文/宗君宏
题记
庚子鼠年,孟夏伊始,前几日还是斜风细雨,过几日便开始放晴,与几位友人相约而定,去完成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活动…徒步秦直道。去瞻仰这千古一帝的雄才大略,挥毫巨作。去领略当时能工巧匠们的良苦用心,鬼斧神工。去追寻古人的踪迹,感受他们的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之场景。去洗礼自己人生道路,感悟生活,感恩社会。
北洛河旁的小村落
太阳还没有从黄土高原的地平线升起,东方的天边隐隐开始泛白的时候,一众人便早早的到预订地方集合,驱车北上,目的地…甘泉县桥镇乡安家沟村。
车顺着弯弯曲曲的沿河公路疾驰而行,太阳的光芒也不知是何时开始铺洒到了对面的山梁之上。是雨后的翠绿,郁葱的山梁云雾开始升腾,闲散的飘逸于山岭之间,眺眼远望,虽没有亭台楼阁做以辉映,但也胜似仙境一般壮美。
熟悉的路途,不一样的旅程,感受各有不同。车过甘泉县桥镇乡后没多久就到了安家沟村,村庄紧临洛河,是个小村庄,几户人家的样子。村旁的整个山崖上刻有“秦直道”三个大字,字为楷书,苍劲有力中不缺中规中矩,圆润厚朴中不乏桀骜不驯。书写者好像是要将这千古奇道用自己的笔力表达出来。表达它的久远,它的的沧桑,它的宏伟,它的俊美。好像要将时间凝固在那一刻,连同自己和这秦直道一样,成为时代的产物。
村庄随小,但却有着大的文章。而这文章就和村旁山崖的那几个大字“秦直道”息息相关。有文记载:“秦直道出甘泉宫北门,穿过墩梁后,即进入甘泉县境内,经高山窑子下山至安家沟村跨过洛河,沿圣马桥北上,经方家河村西北盘山而上,进入志丹境内。”可见举世闻名的秦直道到沿子午岭的山梁北上,来到这里时下山,来到这个洛河旁的小村庄。村旁有圣马桥,直道穿桥而过,继续北上。昔日的大桥早已在风雨的冲刷下,荡然无存,现存引桥依旧耸立在河畔,静待着岁月的轮回。而据考古家考证,这里还有曾经有类似今日停车场及建筑物之类的遗存,不知虚实与否。
此刻,站在洛河岸边,顿时自己好像穿越到那个时代:“一个多雨的季节,南来北往的商贾来到了这里,要么面对滔滔的洛河水涨踌躇难前,要么是盘山道路的泥泞,等待着雨后天晴。此刻,这偏僻的小山村瞬间热闹了,骡马圈内牲畜的嘶叫声,酒馆内的猜拳吆喝声,客栈内无奈的呓语声,……!又仿佛看到了一对对军马列队前行,马蹄飞奔尘飞扬,”
漫步秦直道,觅古始皇帝
直道应是顺着沟内的山坡盘旋而上,但两千多年的风雨中已使其荡然无存,只有现代人修建出的山路,蜿蜒着伸向山梁,走到半山坡时远远望去,见山之巅处,有偌大平地出现,那就是秦直道吗?怀揣着敬畏中的疑虑,提着初行时沉重的双腿,沿着捷径小道向山顶的哪处走去。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脚下的周围,心想说不定时来运转了,还可以捡拾到古人留下来的古董之类的物件儿,以供自己留作念想。因为这条古道几乎伴随了中国封建王朝的一生,怎么会没有了呢!辗转间就来到山顶,但已是气喘吁吁。但好在同行的博物馆杨军好友博古通今,尤其对考古知识尤为通晓,与其并肩同行中谈天说地,倒是驱走了不少的劳累。
山畔之上极目远望,群山碧翠,颠荡起伏。一条平坦的大道清晰可见,犹如一条绿色的丝带,飘逸在这些山梁之上,散发出阵阵古老而又苍厚的气息,弥散着整个山梁。道上有现代人立下的字碑,刻有秦直道字样……这就是秦直道。
忽然,堑山堙谷这几个字又一次闪现在脑海中。《史记.蒙恬列传》记载:“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堙谷后的遗存没发现多少,但堑山的痕迹是明显的烙印在直道旁的山畔上。感叹了……这是多少道山峁多少道梁啊,而且是从河套地区直抵咸阳,在没有现代化的挖掘机,推土机的情况下,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啊!思想也顿时也跟着复杂了起来,赞叹始皇帝的雄才大略,敢为天下之大不为,树千秋万代之功绩。赞叹古人测绘技术的高超,硬生生的从这起伏不平的山梁上找到这么一条能够用以修建道路的串连之处。自豪了,古罗马修建仅仅五米来宽的罗马道让整个欧洲自豪了一千多年,而我们老祖宗修建的这秦直道,早它二百多年不说,且可以让好几辆汽车并排跑,且是用黄土夯筑能够屹立两千多年而不倒,且是改曲为直,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一条高速公路。同时也同情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如此繁重的劳役之下,如同牛羊一般任由驱使,风餐露宿,朝不保夕,或许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生命就如昙花一现,还没有领略河山的壮美,就永远的定格在了这里。你说我们到底是去自豪呢?还是应该去悲哀呢?还是……?
脚下小道在秦直道上延伸,两旁是郁郁葱葱树林,但在秦直道的路面上除了偶尔的地段被附近村民耕为农田外,大部分宽广的路面上只有矮小的野草在阳光的炙烤下苦苦的挣扎着,这是什么道理呢?难道是巫师的诅咒,还是对修直道而故去的人们的一特殊的哀悼?后来见有专家发文报道,说这秦直道上草不过膝的原因是因为在筑路时,将黄土加以烘烤,然后在予以夯筑,才致使杂草树木很难生长。但专家的话只能去做一参考,因为古人的许多智慧很难去用现代人的思维去参透的,那只是一种猜测罢了。
倘徉秦直道,觅古始皇帝,此刻算是真正的走在了秦直道之上了,所领略的不仅仅是秦始皇的才略,而是好像穿越在整个封建王朝之中了。从秦朝建国到清朝的灭亡,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一直是从北方到关中的一条军事与商贸的要道,行走在其上的人马军旅应该是数以亿计了。能没有故事嘛?从始皇帝暴毙,灵柩顺直道而归开始,到汉朝初始,国力微弱,为抵御北方匈奴南侵,开始采用“和亲”政策,一路走来,应是故事不断,目不遐迩。
据现代有史学家研究,著名的昭君出塞和亲时,应该就是沿秦直道北上,到达内蒙古包头附近。一路颠簸一路的眼泪,一路相思一路的无奈。据有书说,子午岭有一处叫打扮梁,就是匈奴迎亲队伍到此地迎接昭君公主,公主在此地拭去伤心的眼泪,重新梳妆打扮,才随着匈奴队伍北去。走在秦直道上,仿佛有看到了昭君公主无数次南望,眼神里充满的是留恋与伤感。
而司马迁随汉武帝北巡后亦从秦直道南归,感叹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司马迁有如此之感慨,可见秦直道工程之浩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走在秦直道上,我仿佛又看到了司马迁骑着毛驴从我脚下的道路南下,东瞧瞧,西看看,说不定也注视着脚下,看看是否有老秦人留下的稀罕物,供自己佐证他史书中的历史。
秦直道对于西汉时期北方的稳定至关重要。有文章分析:“西汉初匈奴六次入侵的路线来分析,关中是匈奴入侵的重点,但严重的侵扰则发生在离秦直道较远的东西两端,如平城之役和朝那进犯。而洛河河谷道和马莲河河谷道却没有受到严重的进攻,推究实际情况,正是秦直道使匈奴有所顾虑。”这充分的体现出了秦直道对北方地区的稳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秦直道这样大动脉输送战略物资的陕北与河套内地区,就像狼牙棒一样伫立于大汉王朝的北方大地,时刻虎视着游牧于塞外漠北的外夷。
秦直道衰落的思考
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本想着这样宏伟的工程定会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大放异彩,但谁又能够知道,过了汉朝就鲜有史书记载,除了唐朝人撰写的《括地志》及《元和郡县志》书籍中寥寥几语外,再有何处有出处呢?这是为什么呢?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难道是史学家忘记了它的存在,还是从隋唐开始就被弃之不用了呢?从此它就像一条苍龙一样横寂于中国的北方…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草原之间。成为了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千古之谜。
有了疑惑就会有人去研究考证与猜测。而据现代许多学者专家考证,这条千古大道虽然自隋唐后离开了史学家的视野,但并没有从此而沉寂下来,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继续发挥着起应有的作用,一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漫漫古道无尽头,行走在其上,也不由自主的开始了自己无厘头般的猜测。据中国古代交通道路记载。“由长安都亭驿西出开远门(长安西城北来第一门)至临皋驿,折北行70里至泾阳县迎冬驿。再东北行经三原县,又折北50里至华原县(今耀县。唐末置耀州)泥阳驿。又北行50里至同官县(今铜川市北),再北历峡道约40里至宜君县,宜君又北约百里至坊州治所中部县(今黄陵县)。坊州东北90里至三川县,由于地当华池、黑原、洛河三水之会,故名三川,置三川驿。又东北略循洛水60里至鄜州治所洛交县(今富县)。(见图4-9-2)。鄜州又北循洛水至秦汉时的雕阴故城。再北行经甘泉40里至野猪峡,为一险隘,又北30里至延州治所肤施县。”以这是史书中记载中通往北方河套地区不同于秦直道的一条新的道路。设身处地于这两条道路之中,究其利弊。秦直道虽然变曲为直,来去快捷,但由于地处山梁之上,远离水源与县城,故面对众多的成群结队的商旅或者军队来说,直道上的驿站很难解决其人马饮水及后勤补给的问题。而新开辟的这条道路,沿途循河谷而行,馆驿众多,从而很好的解决的路途中生活及后勤补给的问题。这是秦直道淡出视野的原因吗?
纯朴的农民
在思考与闲谈中前行,脚下的路也变得不再那么漫长。徒步伊始,就在直道旁遇见一户农家,一中年妇女正坐在一简易的土窑之前做着农活。见我等众人前来,倒是没有陌生人的那种隔阂。几句简短的言语交流后,便显露出陕北人厚朴的本色。“你们走了这么长的路,估计口渴了吧,窑洞内的缸里有水,你们进去喝一点水再走吧!”多么熟悉的语言,这不正是小时候在自己外婆家遇见村子路过陌生人时的话语嘛!心里顿时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而再一追问,才知道他们的水也是从几里路的山下用农用车拉上来的,感激之情无溢于言表。如果这种厚朴只是佹得佹失的小概率事情,那么行进到中午时分,汗流浃背,腰膝酸软之际,又偶遇一羊场,队友上前讨一壶水喝,然羊场主家见我们风尘仆仆的狼狈样子,说道:“你们走了这么远的路,要不在我们这里吃一顿饭,歇一会儿再走吧!”言语中又一次见到了纯朴的神情,或许您又说这是无独有偶的事件。行至夕阳西下时分,又在一山梁之处遇见一家农户,知我们来意,邀请喝水吃饭那都不在话下,而且关心般的说道:“此地距离水磨坪村还很远,你们今天估计已经走出去了,如果不嫌弃我们这里,不如就在我们这里过夜,明日再走!”。呜呼哀哉,一种非亲带故的偶得情谊,让人瞬间甜到了心头。的确那日我们并没有走出事先规划好的这段秦直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依旧行进在秦直道上,或许冥冥上苍的眷顾,让我们又遇到一家农户,就像是看到了最后的一棵救命的稻草一般。一番的沟通后,男主人便开启他家的三轮车送我们出山。没有月色的秦直道上,三轮车拉着我们翻山越岭,在颠簸中前进,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到达我们初始规划的终点站…富县张家湾镇水磨坪村。而费用仅仅只收了60元,这仅仅只是油料的费用吧!感激…感恩一路所遇到的人们。
后记
夜色如墨,群山静籁,车外的世界又一次回归于沉寂,沉寂的好像是世界上的万物都归于它所有!不容一丝的别人一丝的侵扰。偶尔,远处的村庄发出的点点光芒,那也是它挥洒在这夜幕下的斑斓,恩赐给我们这群夜归人的奖赏。风顺着车旁划过,所激起的不是对夜的遐想,而是对这一天的总结与回顾;延展到对人生的思索。何为伟大?…始皇帝伟大吗?不同角度去考量它,结果不同,而我们这些如同蝼蚁一般的小人物,则哀怜的是那些为修建秦直道而早逝的人;唾骂始皇帝为自己的千古帝业,不怜悯他的子民,而最终导致民心离散,帝国大厦毁于一旦。或许也有学者站在民族的高度,去赞美秦朝,赞扬始皇帝,赞美他胸襟开阔,智谋远惠,为中华大一统奠定了基石。
功过是非总是留给后人评论,而我们这些后来者小人物们,又能怎样去评论呢?史书中的记载与与现实中的遗存,依然是在我们的视野中犹如管中窥豹,难究其全貌,也只能是信步秦直道,发出各种各样的感叹。
只是骊山陵墓里的始皇帝已再不能踏上这条北上的战道,而现在新建的高速公路,逢山挖洞,遇河架桥,才是真正的快捷。如果能穿越历史长河,来看现在的中国,那估计也要赞叹了!
作者简介
宗君宏,陕西省吴起人,洛川文学特约作家,医院,爱好广泛,喜欢文学,曾写作过网络小说,并有《洛河流水鸣》、《胜利山的早晨》、《丹青陕北》、《独赏西沟》等多篇散文和短篇小说在各大媒体平台发。
洛川文学社赞赏作者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houpua.com/hpgx/5552.html


